|
|
"即便这样,父亲仍旧读得津津有味、摇头晃脑以至于忘乎所以,仿佛在父亲面前的虚空里聚集了很多幽灵和祖先在听他读书,他一边朗读一边有节奏地打着拍子,只有顶出布鞋的右脚脚趾从破洞里朝外探头探脑,时刻附和着他。"
荒漠图书馆
作者|江 媛
来源:广州文艺杂志
1
去年夏天,妈妈带我们来到这条从砾石戈壁塌陷下去的巨大裂谷,几乎吓住了我们。我们沿着牛羊踩出的小径下到裂谷底部,发现一条清澈的溪水正在大地的裂缝里淙淙流淌。阵阵穿谷风吹起水的气雾扑面而来,令我们遭受烈日炙烤的心魂蒙受润泽。在干旱无垠的荒漠上遇见河流本就是奇迹,更何况这条清可见底的河流不怕死地沿着沙石俱下的谷底一路朝前奔流。站在谷底,我们捧起溪水畅饮,甘甜的冰雪融水滋润了冒火的喉咙,令久经烈日炙烤的我们顿感清凉。我们光着脚在浅溪里戏耍,让鱼群轻轻亲吻脚丫,享受舒服之痒。在流水的伴奏中,妈妈唱的歌谣被深谷的风吹过一道道裂谷的褶皱爬上高耸的绝壁,一直飞到地面上去。在我们头顶的一片碧空里,一只鹰正悬停于高空准备伏击猎物,我们为能深藏深谷而感到安然。这条大地的裂缝藏在绝壁高耸的阴影里,为走过漫长戈壁砾石路的我们提供了歇脚之处。妈妈从长在裂谷里仅有的一棵槐树上摘下槐花塞进提袋,为能获得带有故乡记忆的美味而笑容满面。
妈妈,这水是从哪里来的呀?
这是从昆仑山上流下来的冰雪融水。
昆仑山?
往日的懦弱和对戈壁的诅咒令我们面红耳赤,这得有多大的水才能劈开又干又硬的戈壁,将一条溪流镶嵌进那道深深的裂谷里去呀!
姐,这条河疯了吗?
没疯。它一定是迷路了,找不到家了,才流到这里来的。
我觉得它是戈壁滩的一道伤口,一直在流泪,水面的闪闪银光就是它数不清的眼睛。
虽然我们对这条河流充满敬意,说出来的却都是截然相反的话。妈妈领我们爬上裂谷,走进林中找出那棵系着红绳的胡杨树来到埋着弟弟光的土丘前,哭得痛不欲生。
光,妈来看你了,昨晚我梦见把你抱在怀里,你的眼睛又大又水灵,脸蛋白得透明,看见你的人都说这么漂亮的孩子恐怕留不住,想不到我们真的没能留住你。都怪那个打鱼的张彪,深更半夜朝墙上钉水老鼠皮,把我的光吓得又发烧又抽风……
妈妈哭着把我们拔的大捧红柳花堆在光的坟头,儿子,妈妈没照顾好你,每次想起你,就像有一把刀子在我的心里剜,妈妈真是后悔莫及呀!
妹妹看见妈妈哭,一边抠土朝坟上堆一边跟着哭。三年前,父母把用被子包裹的光草草埋在这棵树下,妈妈曾肝肠寸断地发誓:等我们日后有了钱,一定要打口像样的小棺材把光好好安葬。
妈妈,哥哥还在里面睡觉吗?
弟弟在里面会不会喘不过气来?妹妹拽着妈妈的后衣角说:“晚上哥哥会不会钻出土堆回家来看我们?”
听到我们的问话,妈妈的身子更加剧烈地颤抖起来,眼泪簌簌滴进干裂的土堆里转眼就不见了踪迹。光的早逝打碎了父母延续家族香火的梦想,使身为女孩的我们无地自容,我们时而望着母亲,时而朝四周的荒凉环望。当我们为在空空荡荡的戈壁滩抓不住一物而揪心时,一个黑点从远处缓缓地朝我们移来。
妈妈,好像有人从盐碱滩那边过来了。
我和妹妹指着那个小小的移动的人影,朝妈妈如释重负地喊。妈妈一把拉起我和妹妹爬上一个更高的土丘,手里握紧棍子躲在土丘后望着远处那个渐渐变大的人影在明亮的日光里朝我们走来。
妈妈,是拾荒老爷爷,他还拉了一平板车破烂。
不是破烂,好像是书!好多书!
这个老人是从哪儿弄来这么多书?你爸爸能保住几本书就高兴得不得了……
妈妈放下棍棒长舒一口气,我们为遇见汉人而欢欣鼓舞。那位腰板挺直的老人拖着绑在平板车把手上的麻绳,一步一步走到我们面前来,虽然他衣衫破烂却自带一股凛然之气。我和妹妹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直到看清了他满脸皱纹中溢满汗水的闪光,竟抑制不住喜悦奔下沙丘去迎接他。
老爷爷,你为什么拉这么多书?
老人将平板车架在土堆上,用毛巾擦去汗水,摘下头顶的草帽一边扇风一边笑呵呵地说,我要给这些没有家的书找一个家。
书也要有个家?
当然喽,书也怕风吹,也怕雨淋,也需要人照顾。
爷爷,你要书有什么用?
不看书,眼睛是瞎的。看了书,眼睛亮堂了心里才亮堂。
哦,爷爷,我们也要看书。
我和妹妹围绕平板车,翻着那些被捆成一摞摞的书,妈妈则围着绑在平板车前的一个木箱看来看去。拾荒老人抽出一本带图画的书一页页地翻给我们看,我们有时看书,有时看老人,为他的眼睛滑过一个个字符和一张张图画时透露出的睿智之光而着迷。
老人家,你会做木匠活?
妈妈里里外外摩挲着那个做工精致的木箱,显得心事重重。
是啊,有些书金贵,我捡到好木头就做一个箱子,把这些书放在里面保存。
爷爷,爷爷,你能不能给我弟弟做个木箱,妈妈担心虫子会吃光睡在土堆里的弟弟。
妈妈被戳中了心思,把我们撵到一边,结结巴巴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老人家,我想请你给我夭折的儿子做一口棺材,工钱我不能一下付清……你看能不能让我分几次……
穷困令妈妈窘得满脸通红。老人合上那本画着美妙插画的书,从一个掉漆的皮包里掏出本子和铅笔记下我们全家人的名字,工工整整地写上弟弟的名字、出生及夭亡的日期,又按妈妈的意愿画出小棺材的图样,才收起本子和铅笔对我母亲说,等我给你的宝贝儿子做好了漂亮房子,就给你送来。
老人安慰完母亲,拉起装满书的平板车一步一步沿着裂谷朝西继续赶路。妈妈目送老人往西走了很远,才满怀安慰地带我们赶回家中。
2
我给光定做了一口棺材,而且可以慢慢付钱。
在哪儿,找谁定做的?
哎呀,我忘了问那个老人叫啥住哪儿了!
你没毛病吧,这么大的戈壁滩见到谁你都信,人家骗了你卖钱,你还帮着人家数钱吧!
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我还不是想把儿子好好安葬。
安葬儿子事小,想回沈阳是真吧!
你神经病吧!
咋了,说中你的心事了?
一向警惕的父亲此时神经质达到了顶点,他为一只陌生的脚踩进他的领地而烦躁不安,更担心妈妈离他而去。为了保护领地安全,他宁可无理地将一切威胁杜绝在外。他瞪着妈妈说,有我在,你就别痴心妄想!
听了父亲的话,母亲被激怒了。
你整天疑神疑鬼的。在这个鸟都不下蛋的戈壁滩上,别说碰见坏人了,就是碰见人都难。好不容易遇见个人,你就不能把人家往好里想?
你把人家往好里想,问题是人家都举着刀等着你这种傻瓜上钩呢!
父亲将自行车倒立过来,一边用右手转动脚踏板,一边用左手拿树枝蘸着瓶子里黏稠的机油朝转动的链条上涂抹。母亲在案板前举着菜刀跺得一块块土豆四处飞溅,极力平息着对父亲的愤怒。父亲将涂好机油的自行车正过来,骑着它来来去去跑了好几个来回,最后把自行车扎在门外,独自坐在木桌旁唱着小曲就着大葱蘸酱,把桌上的半瓶白酒喝得精光。
那天,妈妈给弟弟做好新抱被的黄昏,拾荒老人拉着平板车来到了家门前。我和妹妹停下堆沙游戏跑上前去,老人从那件虽然破旧却洗得洁净的衬衫胸兜里给我们掏出两本小人书。我和妹妹翻开小人书,为第一次看到一个陌生的奇异世界而大呼小叫着。
原来,在戈壁滩外面还有这样漂亮的地方和这么多人啊!
那叫城市,有很多人,有很多楼房,还有很多车。
那里一定很远吧?是不是要走出这个铺到地平线的戈壁滩才行?
远着呢,走出戈壁滩后,还要坐车。一直过了玉门关,那儿才叫内地。
哦,那我们这里就是外地了。
我们听着老人说着外面的“神话”,以惊奇的眼神盯着小人书里不可思议的人群和繁华,猛然觉得天地间裂开了一道缝,透过这道缝我们看到了一个全然未知的世界,那里生活着和我们截然不同的人,还有一座挤满人群和房屋的被老爷爷叫作“城市”的地方。
母亲用颤抖的手指着书页说,妈妈的家乡沈阳就是这样,一样的街道一样的楼房……转眼我离开那里已经十几年了,不知道还能不能回去……
不知为什么,看着这些书妈妈突然变得黯然神伤,“我就是在那里出生,在那里长大的,要不是你姥姥去世,我也不会来到这个鬼地方!”
我们猜想父亲千方百计阻挠母亲回沈阳,一定是怕妈妈把他一个人丢在戈壁滩上。
拾荒老人同情母亲的遭遇,小心翼翼地把那口做工精致的小棺材摆在凉棚下的木桌上,接过妈妈端来的一碗白开水和一个玉米面馍馍,坐在小板凳上有些拘谨地小口吃着。我和妹妹摩挲着打磨光滑、红漆光亮的棺材四壁,为它的精致爱不释手。
妈妈转身走进厨房,提出积攒在柳条筐里的二十几个鸡蛋,放在木桌上说,老人家,这次先把这些鸡蛋给你,下次等我们把今年的公鸡带到巴扎上卖了,可以再多给您一点,你可千万别嫌少。
拾荒老人从平板车上取下一块刻着一家人姓名和弟弟光的姓名的石碑交给妈妈,这让妈妈感激得不知所措。
妈妈又从厨房里端出一碗热气腾腾的浮着几片葱花的鸡蛋羹,吹去浮在上面一层飘着油香的蒸汽,将木勺插进嫩黄的鸡蛋羹里,毕恭毕敬地请老人食用。
拾荒老人吃了两勺鸡蛋羹,看着盯着饭碗咽口水的妹妹和我,用勺子舀出鸡蛋羹,一勺喂进妹妹嘴里,一勺喂进我嘴里,直到我们吃得碗底精光,拾荒老人才放下饭碗。
爷爷,能不能把这本小人书送给我们?
爷爷,我也要这本小人书,上面有妈妈的城市和人群。
老人家,我这两个孩子太可怜了,她们生在戈壁滩,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城市,也从来没见过人群……
妈妈一边从柳条筐里往布袋里拾鸡蛋一边说,我想买下这两本书,但钱还是得欠着您……孩子们如果不看书,都变成野孩子了,我担心娃娃们早晚会被戈壁滩吃掉……
母亲朝老人欠身,满含歉意,眼里泪光闪烁,实在是给您添麻烦了……
我把这两本小人书送给娃娃,这书会给娃娃们在戈壁滩点亮两盏灯,不让她们变成睁眼瞎。不过……老人抚摸着妹妹的头说,一定要爱惜,这可是我从火堆里抢出来的。
老人起身接过妈妈装进布袋的鸡蛋说:“明天是个好日子,你好好地重新安葬宝贝儿子吧。”
拾荒老人说完,拉着他的平板车继续赶路。我们把小人书捏得紧紧的,目送老人在起伏的戈壁滩上渐渐走成一个小小的黑点。
第二天一早,妈妈带着我们来到弟弟光的坟前。为了不伤到光,我们用手和圆头的木棍刨出了被装在爸爸做的简陋盒子里的光……干瘪缩小的光的骷髅脸上爬满了小虫,那件包裹光的棉被被虫子蛀得千疮百孔,许多虫蚁从里面进进出出,妈妈拆不开那条和弟弟的肉体长在一起的小棉被,只得点起艾草和芸香的火堆,将光放在火堆中间的土台上熏香驱虫。现在的光和妈妈描述的天使天差地别,我和妹妹惧怕那一小堆缩在布满破洞的抱被里的骷髅,都躲在妈妈的身后,看着妈妈用扇子将点燃的艾蒿和芸香的青烟扇到弟弟光的枯骨上,一群群虫蚁从抱被的洞里成群结队地钻出来,宛若吸饱了光的魂魄般扬长而去,散落到一丛丛红柳和沙棘丛中。
妈妈为光驱完虫,用剪刀剪去与光粘连在一起的破棉被,把那堆遭到无数虫蚁啃食的痛苦的骨头捧进新抱被里裹好,放进那口精致的小棺材里合上盖子,小心地用锤子把一枚枚铁钉钉进盖子,又重新把棺材抱进垫着厚厚艾草的坑里。为了避免虫蚁啃光弟弟那最后的遗骨,妈妈弄来艾草和芸香覆盖棺材,哭着用坎土曼清理砾石挖出下层松软的土掩埋了光,并把那块刻有全家人和光的名字的墓碑竖在了坟前。
光,光……妈妈伤心欲绝地呼叫着弟弟的名字。我们记住了弟弟奋力与死亡搏斗的样子,可怜的弟弟经历无数虫蚁啃食后缩小的枯骨以及因遭遇病痛而变得空茫的眼洞、嘴洞和鼻洞都铭刻在我们记忆里,每想起一次都令人心碎。
此后,妈妈不再提起光,我们也绝口不提,弟弟光的美被无形之贼偷窃得一干二净,以至于我们眼中所见击碎了心中所念。
3
在我们重新埋葬光的第二天,父亲带着一台不知从哪儿弄到的旧收音机回到家中,我和妹妹除了拥有了两本魔幻的小人书外,又拥有了一台能发出各种声音的收音机。当父亲架好简陋的十字天线蹲在地上笨手笨脚地调台时,吱吱啦啦的电波让我们总感觉有个命运的钟摆在世界各地摇摆不定,捕捉着奇异的声音世界。当某个电台出现清晰的声音时,我们又感觉那是幸运之神的钟摆停在了那个地方,打开了那个地方声音的万花筒。当收音机里传来豫剧的婉转女声时,父亲跟着那捏腔拿调的声音摇头晃脑地哼唱并为听到了乡音而一圈一圈地揉搓着自己的肚皮,显得心满意足。这个时候我和妹妹可以干一些平常不敢干的出格的事儿,不会受到父亲的责罚。父亲把收音机的声音开得震天响,那唱得浪声浪气的小妇人简直要从激越的板胡京胡梆子之类的铿锵顿挫声中跳将出来了……这热热闹闹的市井悲喜闹得喜欢昆曲的母亲心乱如麻,她摘下围裙扔到一边,恶狠狠地冲过去拧小了音量,引得父亲狡黠地嘿嘿一笑。
在这个鸟都不下蛋的地方,要待到啥时候才是个头啊!
妈妈把被风吹落在地的衣裳捡起来,重新挂在门前的绳子上,撑平,眯着眼睛朝横亘着深蓝色山脉的地平线望去。
妈妈,等我给戴胜鸟垒好房子,它就会在里面下蛋。
望着妈妈那张苦恼不已的脸,我觉得晾衣绳上随风飞扬的衣裤衬着远处白雪覆盖的蓝山很美。妈妈从麻袋里倒出苦苦草在树桩上剁起来,四处溅落的苦苦草在她飞快扬起又放下的菜刀下溢出乳白色的草汁,散发出浓郁的苦香。五只饿了一夜的鸡从栅栏里伸出尖喙,抖动着鲜红的鸡冠,迫不及待地叫着。
我在沙地上掏出一个洞,又用土块将四周垒起来,催促着玛依拉:“快,快,把它放进来,我把洞口封上。”
玛依拉小心翼翼地捧着我们从墙洞里掏出来的戴胜鸟,把它放进垒好的窝里,我还没把洞口用树枝封上,玛依拉就撒开了手。那只被我们像宝贝一样抱来抱去的戴胜鸟冲翻了我垒的窝,尖叫着振翅朝沙丘前的沙枣林子跌跌撞撞地飞去。
妈妈,这下让你说对了,戴胜鸟跑了,真不会给我们下蛋了。
在我的童年,妈妈的话总能预言成真。比如前几天,邻居张标划着船从盐湖收网回来,妈妈悄声对我说,我看见张标被绳子捆着双手。果然,到了黄昏,镇上来了几个人,用一根绳子拴走了他。过去我一直以为绳子是用来牵驴的,现在我才明白绳子也能用来牵人。
虽然妈妈的预言常常令人吃惊地变为现实,但每次看到那个又瘦又高的拾荒老人在人烟以外不慌不忙地寻找着什么,妈妈总会说,这个人很深沉,实在猜不透,你说他是个捡破烂的吧,他又满脸书生气,有好几次,我看见他从收来的垃圾里挑出一本书,坐在树下一看就是半天,连饿了、渴了都不知道,你说说这个老人是个什么来历?
你管他什么来历?听母亲这样说,父亲嫌母亲多管闲事。
妈妈白了父亲一眼,脸上升起鄙夷的神色。
父亲并不理会母亲,他刚从胡杨林里打到一只野兔,正兴奋地把兔子挂在立柱上,用铁锤乒乒乓乓敲晕了兔子,忙着把黄灰相间的皮毛从热腾腾的兔子身上剥下来。
看到父亲这副没出息的样子,妈妈赌气地将一只喂狗的铁盆扔在死不瞑目的兔子下方,坐在灶边呼呼地拉起了风箱。父亲目光炯炯,一手持锋利的小刀,一手扯着兔子的皮毛,麻利地用小刀从兔子身上一点一点地剥下皮,嘴里呼哧呼哧地喘息着。小刀在兔子的皮肉间沙沙地走动,血从皮肉内渗出来滴进盆里,也淋漓到父亲的蓝布裤脚和花白的黑布鞋上。父亲拽着剥出的白条兔子的腿,将它在滚开的锅里摆了几摆又拽出来,把它吊在挂钩上沥水。为了不与兔子那死不瞑目的眼睛对望,我们都绕开那根挂着兔子的柱子,为那只被剥光皮毛的、可怜的兔子难过。
你说他拾破烂吧,又不全是,他究竟在找什么呢?
这次妈妈有点像是自言自语。父亲从屋内抱出一条狗皮褥子,从上到下铺在门口那张冷冰冰的椅子上,舒舒服服地坐下,开始读他那本虽经一路盲流丢了行李也舍不得丢的书,父亲读着读着,飞溅的吐沫就喷溅到我们的脸上、头上甚至嘴里,父亲洪亮的朗读声有力地敲着我们的耳鼓,好几天都在我们的耳际轰鸣。
父亲突然停下来,看着我们莫名其妙地说,每天我都得像老鹰那样出去给你们觅食,还得像老母鸡那样把你们护在翅膀底下。
对总也吃不饱的我们,父母常常觉得不堪重负。我们总是饿,父亲越读书我们就越觉得饿。每当父亲读到“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我们都会抬起头以寒鸦般的目光望向他,用目光抗议,你骗人!
父亲望着我们这两个饿得想把什么都吞进肚里的孩子,沉默下来。
为了让我们吃饱,父亲只能四处奔命。一天黄昏,沮丧的父亲发现了一只冲着地平线吠叫的野狗立即变得精神焕发,他拿起门后的铁棍,潜伏在那片随时会被扎破脚掌的沙枣树林子里,一动不动地盯着那只瘦骨嶙峋的野狗,生怕错过了捕猎的机会。就这样,父亲日夜蹲守,接连打死了好几只野狗,全部喂进了我们的肚子。我们连撕带扯地抢食完狗肉,父亲就把一张张颜色不同的狗皮用苏打水浸泡后抱到盐湖边冲洗掉血污和油脂,把它们一张张钉在土墙上,任凭它们疼得在大风中簌簌发抖。到了夜晚,我们出来解手,看到土墙上趴着好几只狗,一只只朝着天空蹿,似乎要把天空戳个窟窿,非要咬死要了它们狗命的人才肯罢休。我们又惊又怕,对那一只只趴在墙上的狗时刻敬而远之。后来,父亲把这些皮子钉到旁边那间四处漏风的库房里,我们才算松了口气。
等到这些皮子晾干之后,妈妈就把它们从墙上取下来,坐在门口一张咿咿呀呀的木床上,用结实的麻线把这些黄黑白还有杂色的狗皮缝缀在一起,拼接成一条又长又厚的狗皮褥子。每当母亲在缝狗皮的时候,被烈日暴晒的狗皮似乎苏醒过来,吐出一股浓烈的恶臭冲进我们的鼻子和喉咙久久不散。即便如此,等父亲再次炖好狗肉,我们照样吃得忘乎所以,把恶臭忘得一干二净。
我从来不坐在那张狗皮褥子上,而且能躲多远就躲多远。在那些厚厚的暖洋洋的闪耀着太阳光的毛皮里,我总能听到好几只狗被父亲大棍敲死时凄惨的哀嚎,也总能看见褥子上布满野狗死不瞑目的眼睛,日夜翻着它们白色充血的眼膜绝望地抽动着,从凄惨地哀求变成瞪裂眼眶地狂吠,这狂吠由远及近,时而群嚎时而独吠,时而叫得震耳欲聋,时而又叫得低沉凄恻,令我越来越相信每一条狗都有不死的灵魂。
我们过了几个吃得很饱的冬日,终于把时常挨饿的心安放在身体里,而不再像过去那样因为忍受不了饥饿,没着没落的心总是日夜朝外窥探,为图谋逃出身体的囚笼而备受煎熬。在这段相对安稳的日子里,父亲总会在清晨冲泡一茶缸廉价的砖茶,像个国王那样庄严地坐在窗下,面对窗外一望无际的荒芜,在布满虫洞的木桌上摊开他那本封皮发黄的繁体字书,摇头晃脑地大声朗读起来。他读得津津有味,越读越兴奋,宛若整个戈壁滩都是他声音的疆域,他雄浑的声音遍布每一块砾石、每一株沙棘、每一只鸟雀,甚至每一粒尘埃。父亲越读越起劲,他洪钟似的声音撞击得我们摇摇欲坠的土屋沙沙掉土,吓得平时用锋利的牙齿啃食木柱的小虫成群结队地沿着木柱朝墙缝游去。整个清晨或黄昏,父亲的朗读声在我们的头顶轰鸣、盘旋,涌起声音的浪涛,澎湃过房间的每一个角落,又汇集到一起从敞开的门窗冲出去,吓得一群偷食鸡食的麻雀落荒而逃。
在这片风和四脚蛇的游乐场里,我们可怜的父亲竟找不到一个听众。妈妈一门心思为了填饱我们的肚子而战斗,我和妹妹则为戈壁滩的生灵和植物着迷,看着充满感情朗读的父亲,我们虽然顾不上听他读书,却又不忍心浇灭遭受贫穷折磨的父亲这最后的激情,虽然我们听得有心无心,偶尔还是不忘跟着他读两句,或是插一句嘴,我们惦记着戈壁滩上的野果和奇迹,虽然表面上对父亲满怀崇敬,却从来不向他提问。即便这样,父亲仍旧读得津津有味、摇头晃脑以至于忘乎所以,仿佛在父亲面前的虚空里聚集了很多幽灵和祖先在听他读书,他一边朗读一边有节奏地打着拍子,只有顶出布鞋的右脚脚趾从破洞里朝外探头探脑,时刻附和着他。父亲仿佛是在向世界宣告,他只是暂时被厄运流放在这片戈壁滩上,早晚有一天他会恢复一个读书人的体面,以知识赢得财富和尊重……
(阅读全文,请购买《广州文艺》2022年第3期)
作者简介:
江媛,女,笔名阿月浑子,喀什莎车人。
19岁首次发表诗歌《遗憾》后回到内地。已在《北方文学》《时代文学》《西部》《雨花》《山花》《南方文坛》《广州文艺》等刊发表散文、诗歌百余篇(首);短篇小说30余篇;诗歌、小说评论20余篇;编写剧本若干,其中微电影《回家》获得河南省第六届文学艺术网络文艺类优秀成果奖。
出版诗集《喀什诗稿》、评论集《精神诊断书》。《喀什诗稿》获得郑州市第十八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暨第十五届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
免责声明:如果侵犯了您的权益,请联系站长,我们会及时删除侵权内容,谢谢合作! |
本帖子中包含更多资源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账号?立即注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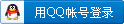
x
|